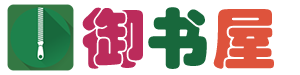第一次摸到枪的时候,我还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猎人。
当然,我也没想过有一天这把枪会成为杀死我哥的凶器。
凶手是我。
这是把契诃夫之枪,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就跟夏以昼说,我的枪术是他教的, 当时我开了个很恶劣的玩笑,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是一部戏剧,你给我这把枪,就得预料到之后某一天我会用上,否则没有必要让它出场。”
“你会用上,”他告诉我,“只要不是对准你自己就好。”
“那如果是对准你呢?”
“那是我活该。”他说。
夏以昼教我用枪的时候他准备去天行市读书,预见到未来我们一年见不上几次面,他说教会我,这样我可以在他不在的时候保护自己——很自以为是,很像他的作风,明明是我说要学的时候他自己凑上来倒贴包食宿也要当我的老师。夏以昼一直喜欢把自己摆在保护者的位置,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他这种习惯从什么时候养成的。后来想想,可能是从我睁开眼睛的那天他对我说他是我哥哥开始。
夏以昼在身为哥哥保护我和维持他的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我不曾察觉的,苦行僧般自虐式奉献的心理准备。
他教会我拿起枪之后没多久就离开,剩下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泡在靶场,发小黎深偶尔会陪我去——我当时猜测是出于医学生的本能,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从我的主治医师,他的老师手里接过我这个能让他发好几篇顶刊病例论文的项目。第一年夏以昼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技术突飞猛进,又得知黎深放弃了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陪我泡在靶场,脸上露出了一种很古怪的表情,一方面可能是不太相信我有这个本事,另一方面是不太理解黎深去靶场能干嘛。
他说黎深射击技术很菜,“当靶子倒是可以。”
黎深表现得很像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样子,虽然只比夏以昼大两岁,但明显更平静,情绪稳定,“未成年人射击需要监护人在场,我只是在替某个失职的监护人履行职责。”有时候我怀疑夏以昼的性格比起黎深看上去更跳只是单纯的兄妹滤镜,他热爱精神攻击身为妹妹的我,而我们的兄妹关系从小到大都这样,在有危险的时候哥哥是挺身而出不顾一切保护妹妹的那个,没有危险的时候,哥哥大概率是造成危险的那个。
夏以昼眉头一皱,“好大的胆子,你敢这么说奶奶。”
相应地,我也喜欢精神攻击他,尤其是站在黎深那边,打出来的效果会翻倍。
我拐了他一下,“我觉得他说的是你。”
黎深:“对。”
夏以昼的脸瞬间就黑了下来,看起来想跟黎深打一架。
我总是会搞不懂黎深和他的关系到底是好还是坏,他们比我大点,我还不懂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青春期,我到了青春期,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跨入了比我更成熟的阶段,年龄之间横亘的差距让我看他们总是有种不清不楚的模糊感,我总是依赖我自己的想象力去弥补他们和我之间的差距。但我的想象力总是有限,他们年纪差不多,还是同龄人里差不多水平的优等生,两个人的名字会一前一后的出现在我奶奶的表扬名单里——我们家里叁个人,我,夏以昼,奶奶,黎深是时不时出现在饭桌上的第四个人。在我简单的逻辑里,他和夏以昼就算当不成朋友,也很难成为仇人。
直到我意识到黎深喜欢我。
夏以昼跟他之间的恩怨实在是很幼稚,一言难尽。这和我小学时候暗恋的学生委员来家里做作业结果被他的黑脸吓跑,初中时候喜欢过的田径队队长在家庭运动比赛的时候输给他不再跟我联系,高中时候的学生会会长给我的表白短信被夏以昼看到后直接代替我回复了拒绝是一样的逻辑。
这是过度保护的副作用,他永远不可能对我的交往对象有好脸色。
但其实他迟早得意识到生活不会总是让人满意,不论是他的,还是我的,我们都没办法让想要保护的人永远远离伤害。就像我们过去一起庆祝过的每一次生日,许愿的长命百岁只是祝福,没有谁会真的觉得,他和我会活到时间的尽头。
我理想化的未来里,至少他要老去,结不结婚无所谓,有没有小孩也无所谓,反正都不影响我们给奶奶养老,然后在他身体机能因为航空飞行而到达极限的那天,我会带着花在他轮椅旁边威胁他如果不听我的话,回头就给他放弃治疗。
这种想法大概是他读大学的那几年产生的,我们之间极其罕见的和谐兄妹情在距离感的辅助下有了质的飞跃,青春期的全能自我意识过去后,我开始意识到他是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未来计划的蓝图里,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他的位置。就算是走在路上随脚一踢的一块石头,最后落地的方向,都要在他的脚边。
不过这个位置,我没想过是他墓碑的位置。
奶奶和他死在2048年的一场起因不明的爆炸里,他还很年轻,奶奶的身体看起来也恢复得还好,意外之前我认为我还能任性至少十年,然后再尝试面对我人生里的第一个生死议题。我们生活里的一千万个可能里,处理各种意外并不在我的遗愿清单里。我总觉得这是极微小的概率,可能就像黎深说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在发生的那一瞬间永远都是1,而我们能够预测的可能性永远都是0,这是确定的,无法更改的。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并面对。
给他们办追悼会之前黎深陪我回去了一趟,遗物经过清理送去了我的公寓,回去看一看只是单纯的缅怀。说起来遗物,实际上没剩什么东西,唯一完好无损的只有我送给夏以昼的项链,写了他的名字的银色金属牌和金属苹果,苹果的中间镶嵌了一颗红宝石,不嵌宝石便宜点,但我还是掏空了积蓄给他买了这块——现在躺在我手心里,深红色的宝石像一滴心口剜下来的血。他的血。
遗物里还有几块奖章,因为被奶奶放在玻璃柜子里展览,又是特殊金属质地,得以在爆炸中幸免于难。里面大部分都写着夏以昼的名字,毕竟是优等生,从小优秀到大,我读书的时候几乎不怎么参加比赛,有我的名字的奖牌都和夏以昼写在一起。
包括我拿到的第一块。
那是夏以昼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他的队友因为意外不能参赛,于是拉着刚进入大学的我当了回替补,直接去参加天行市的射击比赛。我一直说他这个决定很乱来,因为在这之前我没有任何实战经验或者参赛经验,同一批的参赛人员里只有我的介绍牌内容简洁,干净,几乎没有什么字。但他还是硬拉着我上场,说想知道我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在他离开的时候站起来应付我自己的生活。
我当时问他:“这跟比赛有什么关系。”
“因为生活也和比赛差不多啊。”
“赢一次就能决定以后我永远不会输吗?”
“重要的是赢的心态,”他说得跟真的似的,听起来就像廉价的成功学鸡汤,“这不会保证你一直赢,但是可以让我知道,你不会一直输。”
我差点就信了。
实际上当时参赛的我根本没有赢的心态,半决赛我慌得要死,虽然赛场上没什么人看,参赛人员也没人在意一个半路出家的学生,但耳朵就像是开了高精尖模式,能在吵杂的风声和议论声里精准的识别每一道能够影响我的不和谐的声音,检查装备的时候手抖得差点扣了扳机走火。可能是我下意识知道,比赛对夏以昼来说很重要,我怕他的光明未来因为我一个手滑就得多拐个弯。当然,他不会怪我,因为队友是他自己选的,他会怪天怪地怪自己,永远不会怪我。
但是我会。
我们的兄妹可能就是这么奇怪。小时候我讨厌过他,打过架,虽然主要我单方面打他。他手贱,因为我发现他在和我打羽毛球的时候偷偷用evol控制球落地的地方,把我当小狗一样满场溜。我发现之后丢下拍子扑过去在他手上咬了一口,回去跟奶奶告状,他还好意思站在旁边笑。青春期的时候我嫌他有点烦,自我意识高速成长的阶段就这样,对异性亲属公开场合出现在自己身边有种无法形容的尴尬,即使他从小到大都没让我觉得丢人,个子高,长相出众,过了几年长开之后综合素质更是在同龄人群体一骑绝尘。
再大一点我开始嫌他碍事,因为他至少扼杀了我四五段还未成熟的恋爱关系。教我学习我嫌他话多态度很差,自尊心让不想在他嬉皮笑脸的时候承认我还没看懂作业怎么写。陪我长跑我嫌他跑太快,航空署预备役以大欺小,当素描模特我嫌他表情不对,要么乱动,要么就盯着我看得我浑身不自在,怎么都能挑点毛病,除了给我送饭的时候——他做饭真的好吃,这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的相处总有一千一万个不乐意,不高兴,不快乐,但这只是我们人生切片缝隙里不足万分之一的陪衬。
反正吵完了最后还是要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吃饭,他做的饭。
这是夏以昼的错,他对我的情绪应对机制太过于单一,以至于让我总觉得不论我干什么,他都能全盘接受,包括犯错连累他。
他真应该感谢我是有点良心,会自我反省的好妹妹,毕竟总得有个人替他担心,他这种过分宽容的气度,会不会养出来一个搞砸了他璀璨光明的大好前程的白眼狼。
夏以昼当惯了好学生,他肯定不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问我是不是紧张的语气和小时候没什么两样,好像对他来说,这里和平时家门口路过的小卖部没什么不同,而他在问我要不要橱窗里摆着的糖。
换个场子我会回头给他一拳,但是今天我不想他输,嗯了一声之后,很不情不愿地点了个头。
“怕输吗?”
“不怕我输,怕你输。”
“有什么区别。”
“我无所谓输赢,但是你输了我会很不高兴。”
“对我有点信心,就像我对你有信心一样。”
“你什么时候对我有过信心。”每次回来看见我的表情都像是我死了又回来了一样,很难理解这种患得患失的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可能在学校住宿的时候半夜睡不着翻来覆去脑子里已经给我编了几百种死法吧。
我听见他在我身后笑。
我也要被他气笑了,带了个没参加过比赛的拖油瓶站在半决赛赛场上,在上一局移动靶失利,团队分已经落后一截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任何失败的焦虑。明明这把我再有任何失误,我们俩今晚就得空手而归,“一直都有啊,而且你什么时候看过我输。”
我紧张到了极点就开始冷笑,面部肌肉僵硬得抽搐,“估计就是今天。”
“凡事都有第一次,如果是跟你一起输的话听起来也不错。”
“太肉麻了,哥。”
“我是在鼓励你。”
“那你不如直接亲我一口。”
话音落下,他即答,“好啊。”
我的枪刚上膛,头顶一热,他的手扶着我的脑袋一侧,不知道是他的脸颊还是嘴唇,贴在了我的发顶上。我回不了头,因为他按着我,按得很用力,脑袋还紧靠着我的,我以为他要我别走神,盯着靶子,维持比赛的状态,于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我只能听到他的呼吸声。
说起来很奇怪,那时候很多的细节我都忘了,留下印象的只有移动靶失利那瞬间的不安和准备期间的片刻焦躁,之后所有声音就像退潮一样从身体中抽离,不安的情绪犹如鱼群在海中跳跃时泛起的白色的浪,逐渐平息。
我什么都不记得,就记得我们赢了。
(夏以昼、黎深)契科夫之枪
同类推荐:
AV拍摄指南、
献囚(NP高H)、
伪装魔王与祭品勇者(囚禁调教h)、
优质肉棒攻略系统(np高辣文)、
同居(1v1)h、
甜文结局之后(H)、
快穿之撩了男主以后(H)、
背德情事(高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