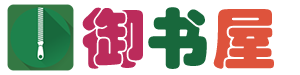“九三年的时候,我们的精力都放在挖掘和论证上面,最后一无所获。”兰朔道,“现在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假设那座古墓确实是存在的,只是像陈先生的经历那样,它后来不在原位了——那么,这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
有人异想天开道:“也许这座墓是移动走了?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国外的新闻,说阿尔卑斯山上有座小木屋,十几年里平移了一千多米,因为它的地基是扎在冰川上的。按照陈先生的说法,他发现墓葬时是洪水季节,那座墓有没有可能是在随着地下水移动?”
“这是不可能的,”立刻有人反驳,“墓葬这种地下建筑,的确有可能会发生沉降或者位移,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过程。几天之内,那座墓就不在原地了,如果它的移动速度这么快,那它内部的结构不可能支撑得住,肯定早就已经被地下水冲垮了。”
谢萦一边敲着键盘记录,一时间不由得无语凝噎,心想一群专家聚在一起,认认真真对玄学事件作分析,这场面宛如鸟儿插着螺旋桨在天上飞……这场面还真得是兰朔才能搞得出来。
一群人脑洞大开地讨论了片刻,间或夹杂着激烈的辩论,最终一致得出了结论——这不可能,任何已知的手段,都不能让一座古墓跑得像一辆长了腿的房车。
会议室里声音渐渐小了,这时有一个人却突然道:“其实,虽然说这不可能,但你们说的这些,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
“当年,挖到七十米还一无所获的时候,我是力主停工的,”他说,“因为我认为,洛阳周边这些地方,根本不具备修建一座这么深的墓葬的条件。”
“这话怎么说?”
“元末明初的时候,洛阳一带发生过一场很重大的地理事件,也就是黄河的第五次大改道,”专家道,“从那以后,洛阳附近的这些地方,黄河几年就要泛滥一次,直到清朝咸丰年间才有所改善。一座那么深的墓葬,少说也要建上几十年,可是明清两代,小浪底地区都经常面对水患,基本上不具备稳定的施工条件,想完成这样一座墓是不可能的。”
有人质疑:“那如果这座墓的年代早于明代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专家摇了摇头,”因为墓葬修到这种深度,对支护结构和深埋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单靠人力用铲子来挖,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但用于挖掘的爆破火药,到了明代以后才出现。这些年,小浪底地区陆陆续续有很多墓葬被发掘出来,从魏晋到隋唐都有,但深度都在三四十米以内。”
“所以说……”专家望向大屏幕上的地形图,有些犹豫地开口,“我当时就认为,小浪底地区不可能存在一座这么深的墓葬。不过,刚才听你们的讨论,我突然就有了个想法,如果这座墓是在别的地方修好、后来移动到小浪底的,似乎一切就说得通了。”
但这种可能刚刚才被众人否决,议论到这里,似乎陷入了僵局。
那位精通风水的邢理事一直插不上话,很无聊地拨动着手指上的铜戒,这时终于笑眯眯地开口缓和气氛:“诸位都喝口茶,我么,不懂这些科学什么的,我就从咱们传统风水和堪舆的角度来讲讲,大家就当听个乐,休息休息。”
“刚才陈先生说的这个故事啊,我听着听着,忽然就灵机一动。我想起来什么了呢?就是他说的那块金砖啊,上面写的前半句,不是缺了些字儿么?我一琢磨,觉得这话听着很是耳熟啊。”
——生■长安,■■泰山,莫■来归■■。
邢理事在纸上写下一句话,身后的会议秘书通过投影仪,把纸条放映到屏幕上。
“生属长安,死归泰山,莫复来归地上。”他抑扬顿挫念了一遍,“这可不是什么好话,这是从汉代传下来的镇墓文哪。咱们一般说给人写个墓志铭,是不是得记一记他有几个老婆孩子,夸夸他生前干了什么好事儿?哪怕是昏君呢,骂他遗臭万年、断子绝孙也就完了,但这句话可不一样。”
众人屏息静听,邢理事乐了:“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活人有活人的地方,死人有死人的归处,你不要再妄想回到阳间。’这是压制凶煞、驱除鬼祟的咒文哪!封墓的金砖上都画满了这种符咒,说明建墓的人绝对不是墓主人的子孙,不然他们跟祖宗得有多大仇啊?”
谢萦敲键盘的手一顿,抬头望向这位福相又富态的老人。
“九几年的时候呢,我也应邀来过。”邢理事继续道,“当时我也分析过,说兰先生失踪的那个地点呢,叫‘玄武垂首,朱雀悲哭’。北方山脉低沉,南方水域开阔,这种地势,是大凶中的大凶的,选作墓葬,会祸及三代。所以当时我就说啊,这个地方是不会建墓葬的,谁家孝子贤孙在这下了一铲子,祖宗都得从棺材里跳起来打他。”
邢理事笑眯眯摸着胡子,玄之又玄道:“现在看来,说不定这两件事还有些相似呢。咱们之前没准陷进一个误区里去了,谁说建墓葬就一定是为了让人入土为安的?如果本来就是为了把人镇压在里面不得超生,那这地方选得简直太对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包含兰朔谢萦在内,众人都听得一脸震惊,而邢理事又笑眯眯地一颔首:“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推测,大家还是相信科学啊,相信科学。各位专家继续吧。”
*
会议在两个半小时之后结束,晚餐就订在酒店的餐厅里,反正自助餐琳琅满目,总有一款能满足你。
专家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用着餐,几个日程紧的已经准备离开了。兰朔与他们简单打过招呼,回到桌前时,发现谢萦面前摆着盘子,却正若有所思地低着头。
她一叉子插进慕斯蛋糕里,也不吃,就挑着里面的红豆内馅往外拨,显得有些心事重重。
兰朔在她对面坐下,语气轻松道:“怎么了,小萦?”
“今天听到的这些,你有什么想法?”
“有很多值得在意的地方,”兰朔道,“只是目前还不能完整地串起来,接下来我们或许还需要单独约见一些人,比如那位邢理事。”
谢萦嗯了一声,继续戳着慕斯蛋糕,几乎已经把它戳得失去了形状。
“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她沉默了半晌,忽然道,“也许,今天所有人说的话,都是对的。”
兰朔抬起头看她。
谢萦终于放下了叉子,她抬起头,脸上没有笑容,表情第一次显得有些严肃。
“有人说古墓可能会移动的时候,你记得其他人是怎么反驳这个想法的么?因为普通地下建筑的结构强度根本保持不住,会被地下水冲垮。但这件事可能很简单,因为那座古墓,也许它是一个'界'”。
四目相对的瞬间,兰朔脸上的笑容也微微凝结了。
一个“界”……
像蚌壳一样包裹着鬼魂的空间,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内部却运转着完全不同的规则。
在西陵峡,他们曾经从一个“界”中归来过……那是藏在水里的一团水,在几十公里的江水里漂流洄游,偶尔浮上江面,制造船难,吃掉几条性命。
——在几十公里的江水里漂流洄游。
如果那座古墓也是相同的情况呢?如果它也一直在地下无声地移动呢?
“‘界’的内部运行独立的规则,里面非常稳定。外面发生什么地质活动和水流侵蚀,里面的砖石结构都不受影响,可以长期保持原状……甚至于,”谢萦的话顿了顿,“陈来福所见到的古墓,与兰若珩所寻找的,极有可能就是同一座。‘界’的形成非常困难,在潼关和洛阳这样的距离里,几乎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
——在潼关,黄河的“几”字形到了转折点,从此奔流而去,在二百公里后抵达洛阳。
地面上,二百公里的黄河一路东流,地面以下,这座古墓像一条顺着暗河载沉载浮的鱼,绝大多数时候沉得很深,但偶尔浮出水面时,有人误打误撞看到了露出来的鱼鳍。
就像水中的“界”只在西陵峡和三峡大坝之间洄游一般,小浪底村对于那座古墓来说,可能是一段地下旅程的终点。
“我们在‘界’中经历的事情,你还记得吧?”谢萦轻声说,“我们离开之后,那团水就顺着江流而去了,你再回到原位,是找不到它的。而当时死掉的那个贼,他的尸体被‘界’卷进去带走了……”
……那个贼的失踪只怕会成为永远的疑案,而对应到兰若珩事件中——
“当年英波吉罗公司的那支地质勘探队伍,”兰朔只觉眉心仿佛在突突直跳,“那二十多个人,他们都被留在了‘界’中?”
所以,随着古墓的离去,他们也就无影无踪地人间蒸发了。搜救队伍地毯式地把整座山搜了个遍,却一无所获。
“我猜是的。”少女半晌才说道,“可能还活着,多半没有,对于一个‘界’来说,你最好祈祷他们当年就已经死了。”
“那么,我叔叔……”
谢萦很轻微地摇了摇头。“他在主动寻找那座墓,说明他肯定是知道内情的,并不是贸然地一头撞进去送死。”
“界”依靠鬼魂的存在而维持,就像包裹着珍珠的蚌壳。除了吞噬误入的生命以外,这个“含珠”的过程几乎不受外界的干扰,直到里面最强大的一只鬼能够破“界”而出时,它就自然而然地失效消散了。
如果像他们在江中之界中见到的那样,失去形体的妖魔占据主导,一众弱小的鬼魂只能依附。一直没有鬼魂能够破界而出,那么这个“界”就会永生永世、永远不变地持续下去。
一个活人,处心积虑主动寻找这座古墓,不可能是闲得没事准备自杀。
难道兰若珩和他们一样,是为了破坏这个“界”,阻止里面的鬼魂修成正果么?可是世界上有没有多一个新的强大鬼魂,和他兰若珩有什么关系,他总不至于也是受了霄的嘱托。
少女慢慢低下头,双手托住下巴,喃喃自语道:“他到底是要干什么?”
古古怪7
同类推荐:
恶龙她只想保命(百合abo)、
末日生存法则(NPH)、
速成炮友(NP)、
(星际)Bad Ending反叛者、
超淫乱美少女(H)、
在恐怖游戏里高潮不断(无限 h)、
【恐怖游戏】人家才没有开外挂(NP)、
平平无奇女beta目睹之怪状(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