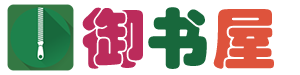知白摆了摆手,却没说话,半晌才道:“那日御医为陛下诊脉,没有说什么?”
文绣有些不解:“御医说陛下略有些风寒,用了一服祛寒的药物也就无事了。陛下自幼习武,身子结实,些许小病并无妨碍的。”
“那陛下无子嗣,御医也不曾说什么?”
文绣顿时被他吓了一跳,这难道是说皇上生不出孩子?这种话说出来,纵然是真话只怕也少不了要倒霉的。
“国师慎言!陛下春秋方盛,不过是忧劳国事少来后宫,才一直不曾有子嗣。且如今宫中人少,历代未有皇帝后宫只三数人的,待来年选秀充实后宫,自然就有子嗣了。”文绣到观星台也一个月了,平常也跟那些小中人们一样,并不能进内殿伺候,还真不知道知白居然什么话都敢说,听他这意思,分明是在质疑齐峻没有子嗣是因为他的身体问题。
文绣心里忽然掠过一丝怀疑——齐峻自幼习武打熬筋骨,与敬安帝那等为金丹和女色掏空的身子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加以他才二十出头,纵然是太后那般急着要抱皇孙的人,也从未怀疑过是齐峻身子有什么不对,只觉得是皇后等人不好生养,偏偏知白却说了这话,莫非他知道什么?还是说那日风雨之中齐峻去寻他,并不只是双手虎口受伤这般简单?
文绣想到这件事情的可能及后果,顿时后背一阵发凉,若是齐峻因此不能再有子嗣可怎么办?那日就是因着她没有看好知白,才——若是太后和皇后知道了,别说她才是个宫人,就算她是妃嫔也一样死无葬身之地!
“国师这话可千万不能再说了!这可是犯大忌讳的事!”
知白不怎么耐烦地摆了摆手,管自沉思去了。文绣心惊胆战地跪坐在一边瞧着他,只见他手指在膝上轻敲,嘴唇微微蠕动,眉头忽而皱起忽而展开,也不知道究竟在做些什么。直到马车将到观星台园门了,文绣才听见知白轻轻自语了一句:“鹿鼠倒是合适。”
“鹿鼠?”文绣莫名其妙,“御苑那里倒是养了鹿,这鼠可……”难道是要老鼠么?还是松鼠?
“哦——”知白又摆了摆手,“我说的是鹿蜀,不是鹿和鼠,乃是一种兽类的名字。”
文绣想了半天,确定自己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鹿蜀——是什么?”
知白心不在焉地边下车边道:“鹿蜀生在杻阳之山,长得像马而白首,身上有虎状斑纹,赤尾,嘶叫起来的声音像谣,其皮毛若配戴于人身上,宜子孙。”
文绣听到“宜子孙”三字,顿时心中一动:“国师是说,这什么鹿蜀的皮毛佩在身上,能,能利于有子嗣?那这东西哪里才寻得到?那杻阳之山在何处?”
知白微微一笑:“杻阳之山么,载于《山海经南山经》,那上头记的都是上古失传之处,如今是寻不到的。”
文绣顿时泄了气,但转念一想又提起了精神:“别人寻不到,国师总能寻得到吧?便是天上的月宫,国师不也带着先帝和皇上去过了吗?”
知白叹了口气:“这却有所不同。月宫尚在,可杻阳之山……鹿蜀只怕更是早已绝迹,若说……或许可用借灵之法。”
“什么叫借灵?”文绣一听有希望,顿时精神更足。
知白有些为难:“皮毛之物借灵却与一般不同,何况这等宜子孙之事,与骨血有关……”
文绣追问:“与骨血有关是何意?莫非是要用谁的骨和血?”
知白沉吟着道:“骨倒不必,血却是必须的……若说最稳妥的法子当然是取到鹿蜀的皮毛,可这实在太难。若用借灵之法,普通之法可用纸画出鹿蜀之形佩于身上,取其吉兆,只是这个法子终在身外,能有几成作用却未可知。还有个法子,就是将这画烧烙于身上,则其灵直达血脉之中,庶几可多几分把握。”
他一边说话一边往内殿走,文绣紧跟着,不知不觉竟跟进了内殿犹不自知:“一张画儿而已,如何能烧烙在身上?”
知白微微一笑:“普通的画儿自然不成,借灵之画却是可以,且能直烙入皮肉血脉之中,只是烧烙之时难免痛苦。”
文绣一惊:“这万万不能!陛下龙体焉可伤损,更不必说烧烙了!”
知白叹了口气:“是啊,所以只好画出来之后让陛下佩戴了。”
文绣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顿时心就砰砰地乱跳起来。她强行按捺住自己,压着声音道:“既是如此,国师几时能作画借灵呢?”
知白想了想:“元旦为一年之首,万物兴盛由一而始,今日便是好日子,还能借几分新春繁衍之兆。”
文绣连忙道:“那奴婢去取笔墨来!”她退出内殿,只觉得心都快要兴奋得从口里跳了出来,果然近水楼台先得月,赵月将她送到这个地方来,原是想着让她远离皇上的,只是赵月绝料不到,居然会亲手送了她这样一次绝好的机会!
55、鹿蜀
“这个便是鹿蜀?”文绣有几分疑惑地将那张纸拿起来看。纸上画着一只似马非马的东西,只有寸把长。知白的画工很是粗糙,比起朝廷惯用的工笔画匠来真是不堪一提,只不过是在纸上涂了个轮廓出来罢了。只是不知怎么的,这画上的兽在烛光下看来却是十分生动,身上那虎状的斑纹似有微光,仿佛在轻轻流动。文绣忽然揉了揉眼睛,不知是不是她的眼睛花了,怎么觉得图上那小东西的鬃毛仿佛在微微飘动。她再仔细看看,正在暗笑自己眼花,就见画中的鹿蜀抬起一只前蹄,轻轻踢了踢。
“这——这东西怎的在动!”文绣惊得失手将纸扔了出去,旁边就是烛火,那宣纸呼地一声就着了起来,吓得她连忙又扑过去抓。可纸这东西沾火即着,她又不敢扔到脚下去踩,拿手扑腾也无用,眼见一大张宣纸烧得焰腾腾的,转头却见知白懒懒坐在那里并不来帮忙,不由急道,“你坐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来帮忙!”
知白殚精竭虑画了半夜,这会儿浑身都乏力,头也昏昏的。西山上九雷天劫,虽然齐峻破着一身龙气替他挡了最后一击,但前头八记天雷到底是将他伤得不轻。他也算是不世出的天赋,在修炼上秀出同侪,加以与齐峻体气相合也是百年难遇的机缘,竟然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一举突破金丹直结元婴。可惜就是因为进境太速,本身根基尚不足以抵挡元婴之劫,若无齐峻出面,九雷天劫十之八九度不过去,轻则元婴重伤修为毁损,重则只怕性命都要赔上。饶是有了齐峻援手,元婴也受了不轻的伤。
不过说来也是有趣,在毁损元气又重新修炼上,知白却比别人有更多的经验。无它,自进京城以来他已经有两三次元气耗损,尤其是移云那次受的伤格外重,因祸得福,这如何修复耗损的元气,他也别有心得,不过一个多月,元婴伤势已然好了大半,这才能借灵鹿蜀。
只是这借灵之事实在耗费心力,到底是伤后,知白这会儿已经昏昏欲睡,见文绣一惊一乍地烧了宣纸,已经有些不耐烦,转听她倒埋怨上了自己,不由得皱了皱眉:“急什么。”他并不是没脾气的木雕泥塑,不过是一心修道,讲究的就是个心平气和,那喜怒哀乐爱怨嗔痴都是六贼所生,皆是要除的,故而轻易不肯动气。加以当初是被齐峻挟迫而来,堂堂太子地位尊崇,手中又握着他的生死,故而就是有气也不敢发,一直这样下来,就连宫人们也都以为国师是没有脾气的了。殊不知今时不同往日,齐峻早也不是对他横眉立目喜怒无常,知白又是在宫内顺风顺水久了,那原来丝毫没有的脾气,如今也长出来一点了,他看惯了齐峻的镇定,这会儿心里就有些看不上文绣一惊一乍的举动,语气之中便有几分不耐烦。
文绣从未听过知白这样说话,纵然是她在西山对知白敷衍了事,也没见知白说句什么,故而一直以为他真是个软面团的性子,虽然被指到观星台来当差,却只觉得是赵月寻机磋磨她罢了,心里真没把知白当个正经主子。到底是在宫里呆久了的大宫女,反应得还算快,一听知白不耐烦了,顿时醒悟自己语气不对,连忙弯下腰去扑火,再不敢说什么。眼看那火焰烧得腾腾的,不过一张宣纸再大也烧不了一时半刻,火苗儿迅速弱了下去,最后只余一堆灰白的纸灰。文绣心疼得仿佛有刀剜了一下,带着哭腔抬头道:“都是奴婢该死,还求国师再画一张吧。”
知白没骨头似地靠在软榻上打了个呵欠:“借灵之事又不是拔白菜,坏了一棵还有一棵,以我道行,也就只有这一张了。”
“可是陛下——”文绣恨不得把自己这只手剁了去,这可是天大的机会,居然,居然就被自己这样生生断送了!
知白睁开一只眼睛,看她当真滚了泪珠,才坏笑了一下:“你在那纸灰里捡捡看。”
文绣一怔,伸手拂开纸灰,却见灰烬里一样东西泛着微光,正是那画上的鹿蜀,原来这一大张宣纸,空白的地方全都烧光了,偏知白画的地方丝毫无损,如今那寸把长的小鹿蜀安然无恙地躺在纸灰里,比用剪子剪下来的还齐整。文绣不由得破涕为笑,连忙捧在手心里:“可吓死奴婢了!”
知白嗤笑:“借灵画出来的物件,岂是普通烛火能烧得掉的?”
文绣紧紧捧着那薄薄的小纸片,闻言忙问道:“既是烧不掉,又如何烧烙到身上呢?”
知白又打了个呵欠,他是真累了,不怎么愿意再跟文绣说话,随口道:“所谓烧烙,并非真用火烧,而是刺肤出血将纸贴上去,其灵入体,痛如烧烙。烧者,血燃也;烙者,深入皮肉也。”伸出手来,“给我罢,明日见了陛下给他佩在身上便是。”
文绣哪里能给他,紧紧捧住了道:“这小小一张纸片,陛下也无法佩戴,不如奴婢去绣个香囊,将这纸片装在其中,也方便陛下携带,国师看如何?”
知白一想也是,遂点了点头,转头扑到床上去睡了。文绣紧捧着这纸片退出内殿,只见天边已然透出一线鱼肚白,正如她的心一般,也看到了光明的前程……
新年第一日,照例是百官朝贺,外命妇们也要入宫向太后和皇后朝贺,宫内宫外都忙得不亦乐乎。今年不同往年,皇上去前朝接受朝贺,连国师也带去了,一时间这后宫里,只剩下贤妃与文充容是没事做的。
贤妃也就罢了,位份既高,皇上也时常往宫里去的,就是后头选了秀,新进来的秀女也没有进宫就封妃的道理,眼见着至少三五年是不必愁什么的,倘若再能生下一子半女,就更不必担忧了。倒是文充容,由昭容而充容,内里的事儿宫人皆知,明白是失了宠的,除非是时来运转咸鱼大翻身,否则新进的秀女们一到,只怕就没她什么事了。宫里这些人个个眼尖得很,故而这一个新年,文充容那宫里是最冷清的。
“这茶水都凉了,大冷天的你上这个冷茶,是想冻死我还是怎么着!”文充容劈手将一个茶盅掷到小宫人脸上,尖声斥骂。
小宫人跪在地上直哭。做主子的不受宠,下人更是没脸。文充容这宫殿本来就偏僻,要用热水还得到隔了两三条夹道的地方去提,纵然那水是滚烫的,提回来也要凉些,更何况烧热水的宫人也捧高踩低,给她的都是滚过了要放凉的水,等提回来沏了茶,不凉才怪呢。
“充容这是怎么了?新年头一日,各宫都张灯结彩图个吉利,充容怎么倒打骂起自己的宫人来了,也不怕晦气?”文绣笑吟吟地打帘子进来,手里捧了个小香袋儿,声音温软,话里却带刺。
新年为图吉利,别说大年初一了,就是正月里都不大打骂宫女,就是怕宫女们哭哭啼啼的冲了喜气,似文充容这样又骂又砸的,别说自己宫里的喜气要被冲了,就连整个皇宫都觉得不吉利。文充容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一时气急了也就顾不上,横竖在自己宫里,想来也没人敢报给皇后或太后知道。没想到文绣这时候跑了来,还这般语带讽刺,文充容的气都憋了好几天了,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一抬眉毛冷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文绣姑娘,今儿国师在前殿呢,文绣姑娘怎不跟着去,好歹也能见皇上一面。”
文绣含笑道:“皇上那日来观星台就说了,前头有文武官员们呢,不叫奴婢过去。”文充容是想说她被贬到了观星台去?真是笑话,在观星台能见到皇上的时候,不比她这冷宫里多得多了!
文充容气得红了眼,咬牙冷笑道:“既这么着,文绣姑娘该在观星台老实呆着才是,到本宫这里来做什么?”
文绣含笑将香囊送上:“这里头是奴婢央着国师写的福字,送来给各宫娘娘们佩戴。贤妃娘娘那里已经送过了,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的还要等朝贺完了才好送过去,就先来了充容这里。这香囊是奴婢的手艺,因是才赶出来的,充容别嫌粗陋才好。”
这分明是说给文充容的就是个拿来凑合事的,文充容积攒了几天的怒气冲头而上,不假思索地抓起手边的茶碟就掷了出去,文绣一躲,那茶碟落在地上砸了个粉碎。文绣似乎被吓着了,脚下一软竟跌坐在地上,手恰好按在碎瓷上,顿时鲜血就涌了出来,手心被划了一道大口子。
旁边的小宫女吓得不行,赶紧上来搀扶,文绣脸色惨白,一边叫她不要害怕,一边用流着血的手伸入怀中要摸帕子,但她把手伸在怀里摸了片刻,突然脸色一变,惨叫一声,飞快地把手抽了出来。小宫女一眼看过去,只见那只春葱般的纤纤玉手此刻像鸡爪一般佝偻在一起,鲜血顺着指缝往外渗,文绣用另一只抓住手腕,似乎是想要藉此止住那钻心的疼痛,却徒劳无功。她凄惨地尖叫着,先是支持不住蜷缩在地,之后甚至忍不住打起滚来。
文充容也被吓得不轻。开始她还以为文绣是在装模作样,直到看到那只已经有些变形的手才发觉不对。那只手上的皮肤仿佛被烧焦一般由白转黄,又由黄转黑,文绣惨厉的尖叫听在耳朵里如同厉鬼夜号,明明是大白天,文充容却硬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抖着手叫宫女:“快,快把她拖出去,请御医!”
御医可不是谁都能请的,按说文充容的位份倒是够的,无奈她不得宠,今日偏偏又是大年初一,若不是要命的大事,谁都不会在今日请御医,故而这一头人去了御医院,那一头太后已经叫芍药过来问话了:“可是充容有什么不适?”
文绣已经叫得喉咙都快哑了。她自以为也是吃得起苦头的,入宫做宫女,谁不是从苦里过来的,小宫女们要伺候大宫女,大宫女要伺候主子,别说犯了错要饿饭、打手板、提铃、打板子等等不一而足,就是没犯错,给主子守夜、伺候也不是什么舒服的活计。可是她实在错料了这小小一张纸的烧烙之苦,竟似是一块烙铁粘在手上,摆也摆不脱。那烙铁里还有无数把刀子,一下下都在往深里挖,似乎要把她的血肉全挖出来,再一点点烧焦成灰。
文充容指着文绣:“是,是她!她——臣妾也不知晓是怎么回事……”她是真弄不明白,文绣满地打滚,三四个宫女都按不住她。芍药见势也吓了一跳,顾不上别人,连忙先去回禀太后。
太后正在寿昌宫里跟几个年长的外命妇说话。她其实不是个善于应酬的人,虽然人都捧着她怪舒服的,可话说多了也有些厌烦,听了芍药在耳边低声说话,不由得微微变了脸色:“新春就在宫里闹成这样?难不成是见了鬼了!”
这话听得下头的命妇们脸色都不大好,哪有大年初一把鬼挂在嘴边的?这些人都是人精子,当即便有人以年老体衰为由起身告退,太后也并不留,打发了人便沉着脸向芍药道:“把人都给哀家带过来!”
芍药再去的时候文绣已经缓过了气来,虽然折腾得冷汗透衣满面涕泪,但那彻骨的疼痛已然消散了。芍药叫人拿个暖轿来抬了她,她便在轿子里胡乱理了理头发抹了抹脸——她要楚楚可怜,可不能肮肮脏脏的招太后厌恶。低头看看掌心,手上的皮肤已经恢复了吹弹可破的纤柔白腻,只留下未干的血渍,掌心里印着一只寸把长的鹿蜀图案,身上的条纹油亮亮的,还轻轻抬了抬前蹄。文绣猛然攥住手,欢喜连胸膛都快冲破了——成了!
“什么?”太后觉得自己好似是在听什么神鬼故事,“你说这个叫什么?”
“此物名为鹿蜀。”文绣跪在当地,声音因为嘶叫太久而沙哑,脸色苍白,头发里还浸着汗水,乍看也像纸剪的一般弱不禁风,“昨夜国师听太后说皇上子嗣不丰,便提到这鹿蜀之皮毛佩于身上可宜子孙……”将知白所说的话一一说过,“因皇上龙体不可伤损,便命奴婢将此物置于香囊之中供皇上悬挂,又亲手写了几个福字给各宫娘娘。”这福字却是她今日一早求着知白写的。
国师_分节阅读_52
同类推荐:
穿成乙女游戏里的路人甲之后(nph)、
诱捕(高H)、
当我嫁人后,剧情突然变得不对劲起来、
恶役千金屡败屡战、
一棵霸王树[仙侠gb]、
小花妖[星际]、
快穿之睡了反派以后(H)、
[西幻]无名的圣女们(nph)、